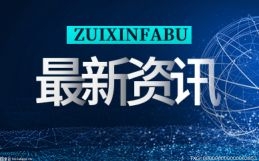中国,是漆树原生地,是大漆的故乡,是世界漆艺的发祥地。
在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遗址中,曾出土的朱漆大碗,就是土古时代使用大漆的证据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大碗
图源网络,侵删
要知道,这可比日本出土的绳文晚期朱漆梳,早了3000-4000多年。
然而遗憾的是,汉唐时大漆工艺传入日本,经过本民族的消化吸收,它逐渐演化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,最终使日本成为西方世界认可的“漆之国”。
甚至它的英文名,被译为了“japan”。
大漆。
很多人初次听到这个名字,都会将它与油漆联系在一起。但事实上,虽然名字里都有“漆”字,他们却相差太多。
油漆,是化学漆,主要原料经化工合成,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苯类物质。
而大漆,是天然植物漆,它是割取漆树后留下的液体,天然,无害,耐腐蚀,防虫蛀。
“漆”,本作“桼”,象形字,上有木,下有水,中间左右一撇一捺,像用刀划开树皮。
这是8000年前古人获取大漆的方法,一直被沿用至今。
每年四月初到八月底,是漆农们上山割漆的时节。
他们早出晚归,找到合适的漆树,再用特制的割漆刀划开树皮,用蚌壳或者树叶做成的茧子接住漆树流出的天然汁液,得到的便是珍贵的生漆。
漆树要生长七年之后才可以进行第一次割漆,割一年,要休息两年。如果一直割的话,漆树就会死掉。
因此,业内常有“百里千刀一斤漆”的说法。
算下来,三千棵漆树一次只能采得一公斤大漆,而一棵漆树的整个生命周期,才能提取十公斤大漆。
生漆
刚刚割下的乳白色生漆,与空气接触后,逐渐氧化变成神秘玄幽的黑色。
“似乌金而非寒,明理堂皇。”
这是大漆的“底色”,也是大漆的“灵魂”。
制作漆灰
制胎、调漆、起肌理、镶嵌、刷漆、荫干、粗磨、细磨、推光、揩清……
制作一件漆器需要上百道工序,每一步都相当耗费时间与精力。
从最初设计、定稿、制胎的反复雕琢,到调漆时成分比例的反复调和,再到在胎骨上变幻出精美绝伦的纹理,每一步都考验着匠人心性,只有心神手法合一才能完成。
朱砂入漆
银珠、石黄、特红、蓝靛、松烟等天然矿物质原料,在大漆的基底之上,不断流淌变幻出美妙的图案。
这种混沌之美,没有太多人为痕迹,美得自然随性,美得浑然天成。
镶嵌
漆干后,还有最考验人的步骤——打磨。
漆层打磨要求十分精细,每一层漆都薄如蝉翼,层层叠叠才变幻出繁复色彩。打磨不及则色彩被掩盖,打磨过头则前功尽弃。
匠人们的双手在毫厘之间反复摩挲,先粗磨,再细磨,最终打磨出金色的漆圈,致密流动,层次分明。
接下来,还要用食用油加上细瓦灰进行手工推光,如此才能让漆面光亮照人、细腻晶莹。
“清如油,明如镜,扯起金钩子,照尽美人头。”
层层工艺之下,完成一件完整的漆器,少则需要两个月,多则需要半年甚至更久。
大自然是无限宽容的,经历了疼痛的收割,繁复的工艺,也让大漆留下了永恒之美。
滴漆入土,千年不腐。坚牢于质,光彩于文。
漆器能耐腐、耐磨、耐酸、耐热、耐溶剂,有着无与伦比的坚硬度和耐久性,也被赋予了永恒的意味。
目前出土的千年漆器中,有很多木胎已经朽烂成灰,但漆层依旧完整,富有光泽。
稀少珍贵的生漆原料和耗时费力的制作过程,让漆器历来就是昂贵的艺术品,过去也只有皇室宫廷、权贵家族才得以享用。
而如今,与大漆相关的十九项传统技艺,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这项发祥于中国,与茶叶、丝绸、瓷器同样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技艺,本就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
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关注致力于大漆技艺的匠人及作品,经过反复的沟通与选择,终于为大家带来了着实令人惊艳的大漆制品。
每一件都造型新颖,工艺精湛,关键是价格也同样漂亮。
并且,我们还为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的赠品福利,购买大漆系列产品满1000元,即赠限量款彩圆滚滚大漆吊坠一条(价值298元,颜色随机)。
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将它们带回家了。
赠品示意图
关键词: